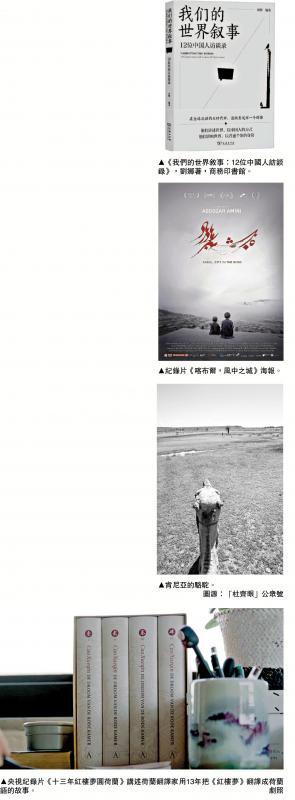
圖:(上至下)《我們的世界敘事:12位中國人訪談錄》,劉娜著,商務印書館。紀錄片《喀布爾,風中之城》海報。肯尼亞的駱駝。\圖源:「杜齊眼」公眾號;央視紀錄片《十三年紅樓夢圓荷蘭》講述荷蘭翻譯家用13年把《紅樓夢》翻譯成荷蘭語的故事。\劇照
當筆者讀完劉娜的《我們的世界敘事:12位中國人訪談錄》時,一群有理想有毅力的故事傳遞者在眼前躍動,一幅以前不曾了解的世界圖景在面前徐徐展開,一種立足於個體的生命體驗講述或建構世界的方式在腦中漸漸清晰。由此,對於書中着意討論的「世界敘事的中國人」和「中國敘事的世界化」這兩個當代文化和傳播中的關鍵命題,也有一些新的認識。/谷中風
如書名所示,「敘事」是本書最重要的關鍵詞。隨着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,隨着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日益捲入全球化浪潮,來自中國的敘事前所未有地參與到世界敘事的創作和競爭之中。作者把敘事者分為職業與非職業,而與新聞機構、職業媒體人、藝術家等相比,非職業敘事者的重要角色值得關注。這一點目前尚未得到系統研究,這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。
世界敘事的普通個體
《我們的世界敘事》聚焦12位在世界各地講述故事的普通中國人,他們是留學生、華人華僑、媒體人、國企外派員工、自由職業者等,跨越了60後、70後、80後和90後四個年齡層,遍布全球多個文化和地理區域。他們以帶着「中國化」底色的理念看待和敘述世界,並以個體世界化的人生經歷見證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互鑒。
從體裁上說,本書是一部訪談集,受訪者娓娓道來的故事,增強了其文學性和可讀性。同時,本書又有透徹而深厚的理論關懷,在某種意義上,本書記錄的每一個受訪者,都是一個看「世界」的角度。比如,自由攝影師張博原說:「每一個人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圓或者一個球。人和人的關係可能就是這些球或者圓,它們或不相幹,或相切,或相交,甚至有的時候是同心。」而這個世界可能是一個不斷膨脹、擴大的圓或者球,「它包含着我們所有人的世界。」前駐外記者韓沖則說:「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推動世界朝某個方向變化的決定性力量,但是我們每個人又都是力量之一。我們不是世界的領袖人物,但是世界的走向最終還是靠每一個具體的個體來推動的。」
這些觀點構成作者和受訪者的共識,以此為基礎,在12個看似個體化的人生故事中,通過受訪者之口以及本書作者的提煉和點評,本書給讀者展現普通敘事個體眼中的「世界」和心中的「世界觀」、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以及描述世界的驅動力、他們講述「世界的故事」時的自我定位,進而幫助讀者深化何為全球化時代敘事、敘事如何改變世界等話題的理論思考。
比如,90後的社會學學者楊雲鬯認為,世界敘事的普及和媒介大眾化,特別是數字媒介的興起息息相關。他還提出「世界這個世界」的命題,也就是把「世界」作為一個動詞,「強調你作為一個人,以你自己的感知和經驗為圓心,用你的身體經驗去感受你周遭所有的一切。」再如紀錄片創作者趙佳認為,「世界故事先得是自己的故事,才能夠成為世界的故事,故事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世界。一個中國農村的故事,如果它有共通性,在另外一個國家的農村也有同樣的人間故事在發生,它可以把世界串起來,增進這個世界的互相理解。」
用影像傳遞故事的信使
本書記錄的12位受訪者中,絕大多數從事與影像有關的工作。其中,杜風彥和齊林是「杜齊眼」公眾號的創作者,也是全球故事的尋找者、記錄者、講述者和傳遞者。杜風彥從小就有環遊世界的夢想,大學畢業後騎車前往世界各地的許多地方。2011年8月起,他用兩年多時間從中國騎行到南非。2022年來到肯尼亞工作。2015年杜風彥認識了齊林,兩人重走非洲,並用照片進行記錄和講述當地故事。
杜風彥的「野心」是讓「被遺忘的人」講述自己的故事。他的合作者齊林認為,杜風彥工作的價值在於把話語權交還給非洲人。此前,如奈飛這樣的國際媒體,「他們的角度實際上不是非洲人的角度,雖然它是在非洲製作、非洲播放,針對非洲人,但話語權不在本地。」用本書作者的話來說,杜風彥「就像一個信使,把陌生人的故事,講述給一路上遇到的陌生人。這些人又把來自遙遠世界的『陌生人的故事』講給身邊的人聽。世界就在故事傳遞的過程中被打開、被講述、被建構。」
與「杜齊眼」相似的另一個影像組織名為「桑拿團」,是英國留學生組成的攝影團體。成員雖然有着不同的學科背景,但有着對人類起源和生存境況的共同關注。對於楊雲鬯來說,攝影是實踐人類學理念和目標的手段;對於張博原來說,攝影是接近真實和身份認同的路徑;而對於「桑拿團」團長雋大鵬而言,攝影是為了追求美好和消除偏見。當他們用鏡頭對準世界,實際上找到一種敘述的新方式,其中第一人稱格外醒目,也因此使個體作為敘述者的意義愈發凸顯。
化身成橋的使命感
在閱讀中,筆者多次被書中反覆出現的「使命感」擊中。多位受訪者都談到「使命感」。留學日本、荷蘭的趙佳本從事醫藥行業,後來「棄醫從影」走上藝術之路。談到自己的轉變時,她說「我有一種使命感。而我從東到西在海外生活30年的經歷,加強了這種使命感」,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,推動世界看到亞洲以及中國這半個世紀來的變化。她與阿富汗導演阿巴紮爾.阿米尼合作的《喀布爾,風中之城》在第17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放映;導演央視紀錄片《十三年紅樓夢圓荷蘭》,講述荷蘭翻譯家用13年把《紅樓夢》翻譯成荷蘭語的故事。本書作者認為,「隻有文化的認同和驅動,能解釋趙佳這種化身成橋的使命感。」
在琵琶演奏家吳蠻的講述中,也可以體會到這種文化驅動的使命感。她從小學習中國樂器,是「馬友友絲綢之路樂團」的重要創始成員。她從小學習中國樂器,開創了多個第一,比如,她是第一個跟紐約愛樂樂團、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的中國傳統樂器演奏家,是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學者獎的中國傳統樂器音樂家,也是第一個獲得格萊美獎的中國音樂家。在世界音樂舞台上,她的名字已經和琵琶聯繫在一起。吳蠻說,她熱愛音樂,有一種對音樂的使命感,同時在國際舞台上也代表着一個民族,她用音樂和世界交流。
這種使命感同樣洋溢在梁子的故事裏,她在2000年第一次去非洲,到2019年底最後一次從非洲回到北京,其間還去了八次印度,四次阿富汗,但她文化上的立足點始終在中國。在書中,她說道:「我覺得有責任把我看到的世界像橋樑一樣傳遞。每一個人都有與他人不同的認識和感受,像一流小溪,匯集起來才能形成一條大河。這千萬個人的不同認知,就是這源遠流長的大世界。」
筆者認為,這一個個被使命感驅動的非職業敘事者,都在與世界平等而放鬆的互動中努力折射出自己的光,而這又將進一步豐富中國與世界的互相理解,並鼓勵人們去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理想世界。




